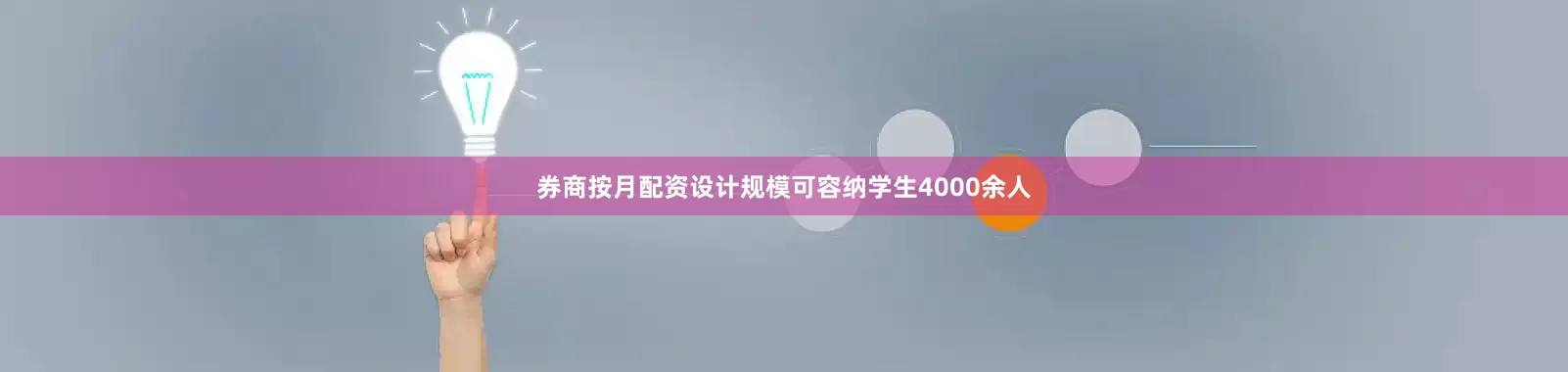1938年的春天,一场震惊中外的胜利在台儿庄书写。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,于这个山东小镇痛击日军,打破了其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然而,这场彪炳史册的大捷背后,却隐藏着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个让人深思的矛盾: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的“杂牌军”,与那些在战局边缘徘徊、最后才“收割战果”的中央军“嫡系部队”,形成了残酷对比。这到底是深谋远虑的战术,还是军队深层的顽疾?我们需要撕开胜利的光环,去审视那段历史的真相。
韩跑跑的“神助攻”
徐州,作为拱卫武汉的战略要冲,其安危直接关乎到整个华中战局。但在1938年初,日军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气势汹汹地直扑山东,局势顿时变得危急。彼时,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手握二十万大军,却选择了让人瞠目结舌的“不战而退”。
他放弃济南、泰安、济宁等重镇,一路狂奔五百里,直接导致徐州门户洞开。日军因此长驱直入,几乎兵不血刃就逼近了滕县和临沂。韩复榘的这一举动,无疑是将毫无准备的中国军队推向了绝境。

面对质问,韩复榘反驳蒋介石南京失守的责任,认为自己并非主要责任人。但最终,他还是被蒋介石以“不遵命令,擅自撤退”的罪名处决,以正军纪。然而,这并不能弥补战线被突然撕开的巨大窟窿,更不能减轻那些被仓促推上前线的“杂牌军”将士们所要承受的巨大压力。他们,成了抵挡日军精锐的肉盾。
滕县:川军铁血铸忠魂
日军来势汹汹,首当其冲的便是滕县。这里,留守的是川军第41军的残部,大约三千名将士,在军长王铭章的率领下,承担起了死守的重任。从2月20日到3月17日,这支被视作“杂牌”的部队,面对的是日军矶谷师团超过一万人的优势兵力,以及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。
装备的悬殊,兵力的劣势,并未让他们退缩。王铭章和他的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,在滕县城内与日军展开了三天半的血战。城池沦陷,部队全军覆没,王铭章也以身殉国。

滕县保卫战,对于整个徐州会战而言,意义非凡。正是这三千川军将士用生命争取来的宝贵时间,才让徐州主战场的中国军队得以集结布防。川军出川抗战,前后三百五十万人,最终仅十三万人归乡,滕县,便是他们为民族牺牲的缩影。
临沂:冤家联手碎敌锋
日军板垣第五师团,作为日军最早编组的甲种师团之一,素来以侵华急先锋著称。他们绕过滕县,直扑临沂。在滕县战事未歇之际,临沂的战火已然燃起。最先抵达这里布防的,是西北军旧部庞炳勋第三军团,兵力约一万三千人。
庞炳勋的部队深知自身与日军精锐在装备上的差距,因此他们巧妙地布设了口袋阵,试图以伏兵战术阻击日军。初期,他们的战术确实奏效,板垣师团遭遇了有效阻击。然而,日军很快便组织起猛烈的反扑,庞部陷入苦战,伤亡剧增,庞炳勋不得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求援。

李宗仁深知临沂的重要性,立刻调派了另一支西北军部队——张自忠的第59军。要知道,庞炳勋和张自忠在当年中原大战时曾是死对头,庞炳勋甚至攻击过张自忠。但民族存亡之际,张自忠毅然放下个人恩怨,昼夜兼程驰援临沂。他采取“以攻代守”的战术,与庞炳勋部内外夹击,对板垣师团造成了重创,使其伤亡近万人,迫使其一度撤退。然而,当张自忠部被调走后,板垣师团又卷土重来,庞部再次受困。直到中央军汤恩伯第20军团派出骑兵团配合反攻,板垣师团才被迫再次撤退,临沂保卫战最终成功,阻击日军长达五十余天。
汤军团的“凌波微步”
在滕县、临沂的血肉搏杀中,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始终在战场边缘“游荡”——那就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,汤恩伯的第20军团。这支部队拥有七万余人,武器装备精良,是国军中的翘楚。然而,在几次关键战役中,汤恩伯部队的表现却饱受友军诟病,被讥讽为“凌波微步”、“乾坤大挪移”。
在滕县激战正酣时,汤恩伯部队并未及时增援。在临沂,尽管最终有骑兵团的“配合反攻”,但其主力部队始终未与板垣师团进行正面硬战。到了台儿庄,他的部队更是坚持“避战保实力”的原则,遇到日军生力军就规避,等待日军主力被消耗殆尽后才打算出击。

李宗仁作为战区总指挥,对此深感不满,多次以电报催促,甚至以蒋介石的授权相威胁,要求汤恩伯出战。然而,汤恩伯似乎深谙蒋介石“保存嫡系实力”的战略意图,始终没有全力以赴,仿佛在等待一个“摘桃子”的最佳时机。这种“军阀思维”在国难当头之际,无疑是对前线浴血奋战将士们的巨大伤害。
血战台儿庄:残师拼死守
1938年3月23日,台儿庄决战进入白热化阶段。日军矶谷师团,尽管得知板垣师团在临沂受挫,却依然狂妄自大,倾巢而出,兵分三路直扑台儿庄。中国军队的防线由孙连仲第二集团军(西北军旧部,仅剩两万四千人,其中第42军已基本打光)担纲,池峰城第31师则坚守核心阵地。
台儿庄内,日军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地狱般的巷战和拉锯战。池峰城率领的第31师,从最初的八千人,锐减到仅剩一千四百人,几乎全军覆没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日军的进攻,守卫着残破的街区。

当部队濒临崩溃时,池峰城向孙连仲请求“给部队留火种”,言语中透露出极度的疲惫与无奈。然而,孙连仲的回答却充满了血性:“士兵打光了,你就自己填上去,你填完了我就自己来填!”他甚至组织了由伙夫、马夫等非战斗人员组成的“敢死队”,高唱着《大刀歌》,夜袭日军阵地,夺回了大部分失地。有明文记载的敢死队就有八批,每批数百人,孙连仲为此投入了十万元。
就在日军主力在台儿庄内被消耗殆尽之际,李宗仁和蒋介石才再三催促汤恩伯部,终于,这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对日军侧翼及后方发动了全线猛攻。在前后夹击之下,日军濑谷支队、坂本支队仓皇撤退,死伤惨重。4月7日拂晓,台儿庄全境收复。
这场战役,国军伤亡约五万人,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被视为“杂牌”的川军、西北军等部队。日军伤亡约两万人,两支精锐师团被打残。台儿庄大捷,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,极大鼓舞了全国的抗战信心,振奋了民族精神。然而,讽刺的是,战后蒋介石却将台儿庄大捷的首功,赏给了在战场上“避战保实力”的汤恩伯。
胜利背后的警示

台儿庄大捷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,它证明了中国军队的血性与不屈。然而,它也像一面镜子,残酷地映照出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:那种“友军大祸临头,我军不动如山”的军阀思维。那些装备简陋、兵员补充困难的“杂牌军”,以其惨重的牺牲和悍不畏死的精神,成为了阻击日军、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。
但与此同时,蒋介石对嫡系部队的偏袒和对他们“避战保实力”行为的默许,甚至将“摘桃子”者评为首功,无疑助长了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,加剧了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之间的矛盾。这种“利用日寇削弱异己”的倾向,在民族存亡的关头,不仅寒了前线将士的心,也严重阻碍了民族统一抗战力量的凝聚。台儿庄的胜利,是人民血肉筑起的丰碑,也是对国民党领导层反思其内部痼疾的沉重警示。这种问题,也预示了兰封会战等后续战役中,类似情况的重演。
网上配资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配资官网张元英生图, 女五一也扛不住贴头皮发型
- 下一篇:没有了